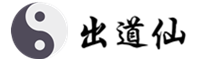立堂口后梦到大客车停着不走(梦见大客车停在路边)
作者:service发布时间:2024-05-17分类:立堂口浏览:9087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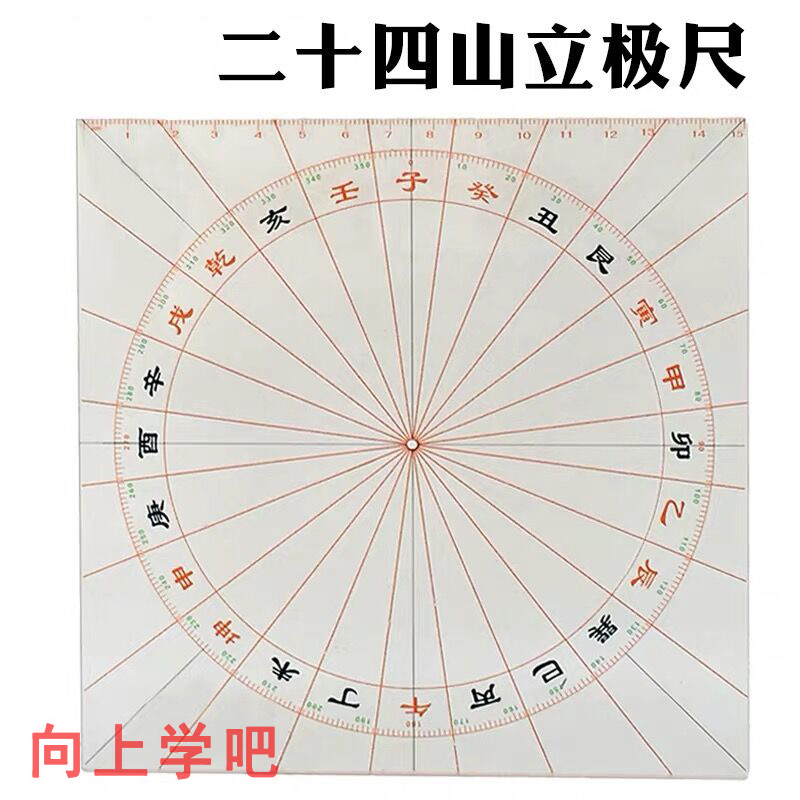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
鲁玉祥,土生土长的普洱人,大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,爱好文学,课余期间喜欢写散文小说,喜欢读乡土文学,先锋文学作家作品,在校期间曾得过图书馆征文比赛一等奖,文学院第八届征文比赛三等奖,大理州美德教育读本《春风化雨》征文优秀奖等。
编者按:
这篇文章在我的邮箱里呆了3个月。今天才看到这篇文字。在选材上,作者选择了自己的事情来写这段生活经历,在写作时,作者应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,情感积蓄,而不能一味地叙述或枯燥地编造故事。虽然他对文字驾驭不是太强,但是,作者的亲情,真情却让我在读的时候热泪盈眶,为他的父亲,也为他的朴实文字而感动。
子卉在《世界上最无私的亲情》第二篇《父亲给儿子的一封信》中说道:扶我一把,用爱耐心帮我走完人生,我将以微笑和始终不变无边无际的爱来回报你。作者用简单明了的创作手法褒扬亲情。虽然,“亲情”是一个抽象的概念,同时,还也让我我察觉到文中的不是父亲“迟钝”,而是我的愚笨,是我没有体会到那沉默背后迸发出来的温暖!
光无声,照亮了大地;爱无言,温暖了心田。父爱,无言。
父亲
大抵我父母那一辈人,讨生活都如此艰辛,这种艰辛也延续到了我人生最初的近十年里。及至今日,梦里仍会无数次的闪现一样的场景,放牛到伸手不见五指,在一间昏暗低矮的土坯房里,点着四十度的灯泡,夜里八九点吃饭,杀的年猪肉总是没挨过半年便不剩丁点,桌上永远都是一素一汤。
这不起眼的土坯木架房是在我父母亲婚后一九九零年建的,我的外公和姑父搭建的木架房梁,我的父母亲一点一点垒起来的土坯。放在崇尚“简约为美”的今天,俨然简约得“过份”。
父亲崇信棍棒出孝子,家法严苛,房门后永远摆着一根木棍。我犯错便被罚“跪堂”,头顶一盆水跪在堂屋里,大有让列祖列宗监督我改错的“意味”。一次放牛的时候我睡着了,牛进了别人家的玉米地里,糟蹋了约几袋收成的量。父亲大怒,对我棍棒交加,我顿时泪如雨下,大喊着:“我不服,我没错,我又不是故意的,谁不会走神睡着啊!你不会吗?”,“叫你顶嘴,叫你睡觉!”我只觉得身上火辣辣的疼。
我在堂屋里规规矩矩的顶着水盆,父亲出去的那一会儿,我赶紧起身蹑手蹑脚的翻出家里的常备消炎药,“红药水”,我对它再熟悉不过,刚涂上的时候其颜色暗红如血状,时久而变紫色。我含了一大口,把手臂悄悄的涂上一条一条的红印。父亲进来看了我一眼说:“知错了没有?”,我仰起头,口一张一合红药水顺着嘴巴流了下来,我以为佯装受重伤父亲会放过我。父亲瞥了我一眼,举起手里的木棍打下来,我一个踉跄把水盆往旁边一扣,撒腿就跑,一路狂奔。
后来,尽管我颇具“英勇就义”的慷慨气度,但作为家中的权威,我多不敢忤逆,我是忌惮的。那时候我恨他,恨他如此暴虐蛮横,毫无舐犊情深可言。在他的棍棒之下,有时好几天我都不与他说上一句话,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父子间有时会如此的剑拔弩张。
二零零零年时,家里唯一的经济收入是采松脂。采脂时,我背着水壶跟着父亲入山,大约一个月收集一次松脂,家里没有农用拖拉机,父亲一担一担的挑着五十公斤的松脂走约二十里的山路,将松脂挑到松脂收集站,每公斤几毛钱,每担最多的时候二十来块钱。我亦步亦趋的跟在父亲的后面,背着水。这挥汗如雨的漫漫长路,两个人总不至显得那么的冷清孤寂。每次卖完松脂走的都是夜路,很冷。我趴在父亲的背上,他左手托着我,右肩担着油桶,我举着若有若无的明子火,火光忽明忽暗的,父亲和我的背影显的异常高大壮硕,时而在某个转角处被拉扯的老长老长,在夜里如鬼魅一般。父亲的汗水味深深的浸入我的每一分学费里,看着父亲我觉得异常踏实,有他的一天,我有学上。
那晚停电,父亲用油漆罐做了三个煤油灯,我和父亲进了爷爷的睡房,借着微弱的灯光给爷爷净身,入殓,村里的先生帮忙占卜,推算出殡入土回煞的日子,忙了一夜。天微亮,父亲拉着我挨家挨户的敲门,磕头,“请帮帮忙,家里的老人不在了。”天明,稀稀拉拉帮忙的人才到齐。我第一次见父亲哭,哭了很久,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。我深深的感受到这座威严冷峻的山峰所透露出来的沉闷哀伤。 大伯从背包里取出一支钢笔,就着我家的桌子写东西。那时候,我写的字一个约一寸大小,一串一串的像营养极其不均衡的山葡萄,挂在我那摸的黑不溜秋的小楷作业本上,毫无美感可言,在大伯秀气漂亮的字面前,我的字就像褪去了毛的秃鸡见了孔雀。其实我无心比较谁的字秀美隽永,我在意的是他手中的那支钢笔,我大伯告诉我说:“漂亮吗?你爷爷送我的,滇西抗战时,一队国民党部队途径我们的村寨,从我们家老房子门口过。你爷爷动用了三斗黄豆作马粮和军官换下的钢笔,笔头是镀金的。”“镀金?真宝贝,我看看。”我边轻柔的抚摸着边说。打那支钢笔在我面前露了一次面起,我对它尤为痴迷,稀罕,我已无心其他的稀奇玩意儿。我缠着父亲给我买了一只金黄色的英雄牌钢笔,这次父亲没有打我。
小河弯弯曲曲从山尖缓缓的流淌到寨脚,水温正好。一阵一阵的风吹过那片田垅,绿油油的稻苗此起彼伏翻滚着,青的发亮。我小心翼翼牵着牛走过田埂,闻着稻苗的清香,大水牛时不时停下脚步,晃了晃脑袋,粗长有力的尾巴往臀部甩了甩,两只向外呲着白毛的耳朵扇了扇绕着它的水蚊,又继续走,终于走完了那片田垅。
父亲五千块钱卖掉了家里耕地的四条大水牛,加上一千块的卖猪钱买了一辆拖拉机,和一座金牛牌的耕地机车。父亲开始学着驾驶新时代的高效率农用工具,处处充满了违和感。他几十年如一日,早已用惯了铁犁木耙,通人性的大水牛从不会违背指令左右乱跑,但机械听不懂他的话。
父亲每天在村里的沙石路上摇摇晃晃的扭着拖拉机的方向架,神情凝重,一脸苦涩。我跟在父亲的后面,时时刻刻为父亲判断路线是否偏移安全范围,“爸!爸!踩刹车,往左打方向啊,后轮都偏了,快点呐,换一档啊!”。村里的青壮年小伙子,站在路边的土坎上大笑,这个时候是我最引以自豪和羞愧的,我自豪成了父亲的最重要的帮手,羞愧父亲有些笨拙,拖拉机开的一塌糊涂,我自信那一刻的我如若再身强力壮些,开的不比村里任何一位老手差。
终于,父亲学会了开拖拉机,春耕的时候我和父亲合力把耕地机抬上拖拉机机厢,拉到水田和玉米地里,耕田耙地。地边并排伫立着树皮棕黄,裂纹遍布的几棵老树,在淡蓝的天空,晶莹透亮的早露陪衬下,抽出温暖的嫩叶。我与父亲并排坐在屋棚里,他一口一口吸着旱烟,往复吞吐,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,这个威严的汉子,平静轻声的告诉我,他原本可以上师范院校,但家里实在无法支撑“高昂”的食宿费,从此一辈子与铁犁木耙青山大地为伴。
父亲又开着拖拉机进城买回了家里真正意义上的电视,那台需要父亲亲手搭建,时常调试天线的老旧黑白电视被一台五十四寸的长虹牌电视取代,家门口立起的可以随意转台的村村通天线,成为我们家的新宠。
拖拉机接送孩子上学在乡下俨然是一件时髦又体面的事情,多年后这样的时兴才被方便快捷的摩托车取代。每到周末,村完小的黄土空地上总会停着老旧或崭新的拖拉机,成群结队的孩子呼啦啦地涌上拖拉机车厢,堪比城中挤公交。就这样,父亲开着拖拉机承载起了我一步一步走出大山的梦想。
我常常在笔记本里写下太多的忆苦思甜,时常回忆起的那些日子,无不与我的父亲相关。在上初中以前,强烈且唯一的愿望是有一双真正意义上的布鞋,不磨脚,暖和。
那时候,我和弟弟身上穿的是姑妈和姨妈家表哥们的旧衣服。每到周末,我和弟弟缠着父亲,“爸,爸,我们的凉鞋坏了。”父亲和我们围在火塘旁,将塑料空药瓶裁成一条一条的“补丁”,用烧得发红的铁锯条软化,焊接起凉鞋的断裂口,冷却后接着穿,一双凉鞋断了又焊焊了又断,年复一年如此。再到后来家里经济逐渐好转,我们穿上了不同版式,不同材质,不同品牌的鞋子,我渐渐开始敬佩和怀念起父亲精湛的修鞋技艺。
母亲精心地用保温盒盛了满满的鸡汤和腊肉,再让父亲坐一个小时的城乡客车送到城里,每次我和父亲固定的坐在一条小巷里的早点铺,他给我叫一大碗面条后就坐在狭窄的长桌对面静静地看着我吃,“爸,你也吃,我一个吃不完。”“我和你妈吃过了,你读书累,多吃一点。”突然,我避开父亲的脸颊,看了看窗外。

有人说每个男孩成长为男人之前首先要打败的第一个男人是父亲,毫无疑问我在学识和身体上终于打败了父亲,从前宽厚的臂膀和胸膛,在我面前显得异常瘦弱不堪。“爸,我来吧。”我挤在父亲的前面,扛走装了满满的咖啡豆的麻袋。
欢迎原创 谢谢赞赏
赞赏
人赞赏